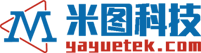古籍文献研究中的“汉籍”

摘要:在现代文献中,“汉籍”一词出现频率颇高,却罕有辞书收录之;学术界均以“汉籍”指称中国典籍,然此义项非中国固有。在中国语境里,扬雄《方言》最早使用“汉籍”,尔后从魏晋至隋唐,再经宋元至明清,汉籍即“汉代典籍”之义项传续千有余年。在日本文脉中,“汉籍”相对“国书”指中国书籍,相对“和书”泛指汉文典籍,又相对“佛书”专指儒学经典。现代汉语中的“汉籍”,既传承古汉语基因,又吸纳日语词血液,熔铸出一个新词——不仅包括中国传统的经史子集,还涵盖佛经及章疏乃至简帛、碑刻、尺牍、图赞之属。当今方兴未艾的“域外汉籍”研究,论者各自定义、随意取舍,呈现种种乱相。若从“汉籍”乃中华文明结晶推演,“域外汉籍”应定义为凝聚域外人士心智的汉文书籍,是在中华文明浸润下激发的文化创新,构成东亚“和而不同”的独特文明景观。
以汉唐为标帜的中国文化,曾经惠及四邻、泽被东亚,由民族文化发展为区域文化乃至国际文化。时逢中华民族崛起之盛世,际会传统文化复兴之佳季,追寻汉风唐韵之海外流绪,大致可分三个层次:(1)中国文化在域外的传播;(2)中国文化对域外文化的影响;(3)中国文化激发域外文化的创新。
中国文化对域外的影响,由衣裳而化为肌肤,再溶为骨骼与血肉,是个由浅入深、由表及里的历程。因之,我们的研究不能浅尝辄止,停留在第一层次,或踌躇于第二层次,应该深入至第三层次,最大限度地拓展中国文化的国际化意蕴。
书籍之路
大而言之,中国文化包含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,前者以丝绸为典型标志,在东西方之间架构起“丝绸之路”;后者以书籍为主要载体,在东亚地区开辟出“书籍之路”。尤其在中日之间,由于大海阻隔和官方交通短暂,近代以前人员往来极度稀少,书籍遂成为日本汲取中国文化的主要媒介。
以书籍为主线追踪中日文化交流史事,国内外学术界已经做了大量前期工作。比如,北京大学严绍璗的《日藏汉籍善本书录》(中华书局,2007年版,获教育部第五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),搜括日本蒐藏的中国古籍万余种,属于第一层次经典;再如,王勇主编的《中日汉籍交流史论》(杭州大学出版社,1992年版,获教育部首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),考索中国典籍对日本的多维影响,归为第二层次作品。至于第三层次,虽然日本深受中国文化熏陶,历代学人用汉文撰写了大量书籍,其总量或以万计,却尚未见规范整理与系统研究
中外学者的大量研究成果显示,书籍之路并非中国文化一味输出的单行道;五代开始的“佚书回流”,证明这是一条互有往来的双通道;倘若从东亚全局来考察,或许称之为“环流”更为贴切。亦即在东亚区域内,书籍交流呈现循环往复、纵横交错的多层次立体样态。
进而言之,文化交流的真谛,不仅在于传播的广度,更体现在影响的深度。以书籍为例,域外人士通过阅读中国典籍而受其熏陶或获得灵感,遂激发模仿与创新的欲念,取范汉文形式以吐露本民族心声,营造出崭新的文明景观。这既是书籍之路在空间的拓伸,也是中国文化国际化意蕴的展现。近年“域外汉籍”研究的勃兴,说明学术界开始关注这一领域。
域外汉籍
“域外汉籍”研究的兴起,至今不过30年。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,台湾联合报文化基金会多次举办“中国域外汉籍”国际学术会议。此风气之先乍开,“以往汉学家们不曾注意,或是根本生疏的”领域,骤然引起国内学术界关注。这一时期,台湾学者开拓甚勤,造势最力。如林明德编《韩国汉文小说全集》(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,1980年),陈庆浩、王三庆编《越南汉文小说丛刊》(法国远东学院,1987年),加上其后王三庆编的《日本汉文小说丛刊》(学生书局,2003年),为“域外汉文小说”研究奠定基础。
大陆方面虽起步稍晚,但从90年代开始迎头追赶,一批具有外语背景的中青年学者加入垦荒者行列,他们与国学各分野专家合作,推出一系列原创成果,此为第一期;进入新世纪呈后来居上之势,无论研究思路抑或涉猎范围以及成果数量和质量,逐渐占据学术制高点并引领学界潮流,是为第二期。下面依次简述之。
首先是第一期。1989年杭州大学成立日本文化研究中心,研究重点定位于“以书籍为纽带的中日文化交流”。1990年陆坚、王勇主编《中国典籍在日本的流传与影响》,提出以“汉字文化圈”为视域之汉籍研究应具备三要素,即“海外佚书”、“中国典籍的影响”、“域外典籍”;1992年王勇主编《中日汉籍交流史论》,倡导“汉籍宏观研究”,设专章探讨域外的汉文典籍;1997年王宝平编纂《中国馆藏日人汉文书目》,收录总数达2671种,基本网罗了留存中国的日本汉籍;加之,2004年王勇主持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项目“中国翻刻的日本汉籍”,成果汇编成《中国馆藏华刻本目录》,收录书目376种。在此基础上,王勇提出“书籍之路”构想,力图构建东亚文化交流新模式
其次是第二期。2000年南京大学成立域外汉籍研究所,自2005年张伯伟主编的《域外汉籍研究集刊》陆续问世,把域外汉籍研究推向一个高潮。会议方面,2006年浙江工商大学与日本二松学舍大学“日本汉文学研究”国家基地联袂举办“书籍之路与文化交流”国际学术研讨会,来自日本、韩国、美国、英国、比利时、泰国、越南的国外学者达41名,“域外汉籍”成为东西方学者共同关注的热点;2007年南京大学召开“域外汉籍研究”国际学术研讨会,国内外80余名学者汇聚一堂,探讨涉及“域外汉籍”方方面面的问题。项目方面,2002年上海师范大学孙逊领衔国家社科基金项目“域外汉文小说整理与研究”,2006年中国社科院历史所主持的“域外汉籍珍本文库”列入国家“十一五”重点出版工程。文献整理方面,2008年人民出版社与西南师大出版社联手打造《域外汉籍珍本文库》,2010年复旦大学出版社推出《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》,2011年《域外汉文小说大系》、《韩国汉文燕行文献选编》分别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和复旦大学出版社刊印出版。研究著作方面,王晓平著《亚洲汉文学》(天津人民出版社,2001年)、王勇等著《中日“书籍之路”研究》(北京图书馆出版社,2003年)、吕浩著《篆隶万象名义研究》(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6年)、金成宇著《域外汉籍丛考》(中华书局,2007年)、张伯伟著《东亚汉籍研究论集》(台湾大学出版中心,2007年)、王勇编《书籍之路与文化交流》(上海辞书出版社,2009年)等先后问世。
由此可知,域外汉籍研究发轫于台湾而盛行于大陆,由小说为主而扩展至经史子集,从学术兴趣而提升至国家行为,从而催生出一门崭新的学科。
仁智各见
“域外汉籍”作为一门交叉学科,虽然诞生伊始,但已呈显学之势。各路精英学术背景既不同,概念定义自相异。
比如,台湾联合报文化基金会在1987年12月刊行的首届会议论文集中,开宗明义归纳会议的三个主题:“(一)有关中国域外汉籍的流传、出版与版本等问题的;(二)有关中国域外汉籍现存情形与研究概况等问题的;(三)有关中国域外汉籍史料价值以及中国与亚洲各国当年关系等问题的。”
再如,王勇于1990年撰写的《汉籍与汉字文化圈》一文,对“域外汉籍”诠释如下:“汉字文化圈诸国在摄取和消化中国文化的同时,历代留下大量汉文典籍,这些出自域外人之手的汉籍,不断丰富着汉字文化的内涵。域外汉籍至今仍是一座有待发掘的宝库,其中蕴藏着令人惊叹的汉文化遗产。……域外汉籍既与中国文化一脉相承,又与本土文化血肉相连,这无疑是汉籍研究的一个全新的领域。”
然而,进入新世纪以后,随着域外汉籍研究渐成气候,吸引各专业学者参与其中,尤其是文献学、历史学、文学等学科领域的学者,依托自身擅长的专业对“域外汉籍”作了独到的释义。
首先,南京大学中文系张伯伟教授,他把域外汉籍概括为三类:“1.历史上域外人士用汉文书写的典籍,这些人包括朝鲜半岛、日本、琉球、越南、马来半岛等地的知识人,以及十七世纪以来欧美的传教士;2.中国汉文典籍的域外刊本或抄本,比如大量现存的中国古籍的和刻本、朝鲜本、越南本等,以及许多域外人士对中国古籍的选本、注本和评本;3.流失在域外的中国汉文古籍。”
其次,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所主持编撰的《域外汉籍珍本文库》,其《编纂凡例》也框定了三部分内容:(1)中国历史上流失到海外的汉文著述;(2)域外翻刻、整理、注释的汉文著作;(3)原采用汉字的国家与地区学人用汉文撰写的、与汉文化有关的著述。
两相比较,虽然排列秩序有所不同,“域外所存的中国典籍”、“域外刊刻抄写的中国典籍”属于基本相同义项,而“域外人士撰写的汉文著作”则稍有不同,即《域外汉籍珍本文库》收录本限于“与汉文化有关的著述”。我们从“域外汉籍”作为独立的学科、新辟的领域来考量,上述定义尚有值得商榷之处。
先说“域外所存的中国典籍”。中国典籍至迟在两汉已然形成专学,从汉儒到宋学再朴学,数千年来师承有序;由校雠及训诂至考据,学风蔚然成型。这里所指的“域外”,仅仅是个空间概念,以此类推的话,既然同一本书籍按收藏国而别为“日本汉籍”、“韩国汉籍”、“越南汉籍”等,那么是否也可按存放地而分成“北京汉籍”、“浙江汉籍”、“福建汉籍”等等?窃以为同一种书因分置不同地域,不足于将其另立门户。而且我们知道,有些域外汉籍如静嘉堂的“皕宋楼”旧藏之类,是近代甚至现代才作为商品流出海外,作为“中国汉籍”研究才顺理成章。
再说“域外刊刻抄写的中国典籍”。张伯伟提到包括“域外人士对中国古籍的选本、注本和评本”,《域外汉籍珍本文库》还增加了“注释”本,即所谓的和刻本、朝鲜本、越南本之类。据日本学者长泽规矩也《和刻本汉籍分类目录》,中国典籍在日本刊刻,分和刻本与翻刻本两种,原书的白文再刻本属翻刻本,再刻时添加训点、假名则为和刻本;日本再刻时添加的音符、旁批、夹注等超过一定限度,或书名冠以“改订”、“增补”、“景印”之类,一概算作“日本汉籍”。以此论之,和刻本大抵居于中国汉籍与日本汉籍之间。然而,据笔者经眼,有些冠以“景印”而归为“日本汉籍”者,本文一如原书;有些书名照旧而划入“和刻本”者,不仅增加序跋,甚至增删作品或添加图版。因此辨别困难,不妨单独立项为宜。
最后谈“域外人士撰写的汉文著作”。按照长泽规矩也的界定,日本人的意匠融入和刻本且达到一定数量,即可将之归为日本汉籍;这与国内部分学者把“选本、注本和评本”乃至“注释”本,一并划入和刻本范畴,显然不尽相同。笔者曾参与日本国文学研究资料馆项目,在中日两国公私图书馆查阅和刻本多年,时有发现在日本人刊写的中国书籍中,注释、批语、考据的文字往往超过原书,如果按现代行规排版,或许可算作一部新书,与仅仅为了助读原文而添加训点、假名的和刻本迥然相异,因而长泽规矩也的界定不能漠视。倘若这类书尚有商榷余地,那么完全由域外人士用汉语撰写的书籍,归入此类当无疑义。至于《域外汉籍珍本文库》所称域外汉籍限于“与汉文化有关的著述”,从内容的角度看,数以万计的日本汉文典籍,基本多属中日文化交融的结晶,欲分辨是否“与汉文化有关”,几乎不太可能。
在上述三种“域外汉籍”中,张伯伟认为主体是第一类,即“域外人士用汉文撰写的各种思想、历史、文学、宗教、艺术等方面的典籍”,这也是笔者主张应该重点研究的第三层次。如果将留存海外的中国典籍比喻为“衣裳”,和刻本类乎“肌肤”,那么日本汉籍相当于“骨骼与血肉”——虽属日本土生土长,但隐藏着中国文化的遗传基因。
“汉籍”新释
如前所述,“域外所存的中国典籍”之“域外”,是个空间定语,表示“汉籍”的存储地;“域外人士撰写的汉文著作”之“域外”,是个行为主语,表示“汉籍”的创作者。前者重在“汉籍”,后者要在“域外”,两者不可等量齐观而置乎同一平台。既然这是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,我们不妨在时空轴中为之重新诠释定义。
“域外汉籍”诞生不久,业外人士或许觉得陌生;至于“汉籍”两字,大概都耳熟能详。其实“汉籍”的古义,失传已久;而现在使用的概念,有可能是近代舶来之物。笔者曾探其由来,先查《现代汉语词典》、《古汉语词典》,继翻《辞海》、《辞源》,再阅《中国古文献辞典》、《康熙字典》,均未见收录。追踪至《汉语大词典》(汉语大词典出版社,1993年)、《中文大辞典》([台]中国文化研究所,1968年),终于如愿以偿,但释义颇令人意外。如《汉语大词典》有两个释项:(1)汉代典籍;(2)外国人特别是日本人称中国汉文典籍。
也就是说,“汉籍”的原义指汉代的典籍,犹如“唐诗”指唐代之诗、“宋词”称宋代之词,此处的“汉”是朝代名而非国家或民族名。《中文大辞典》在此义项引《宋书•历志》:“远考唐典,近征汉籍。”这是祖冲之上表文中的一段,以上古之“唐典”(如《尚书》中提到的“虞书”、“夏书”、“商书”之类)对应近代之“汉籍”。据笔者考索,最早的用例大概出自汉代扬雄《答刘歆书》:“其不劳戎马高车,令人君坐帏幕之中,知绝遐异俗之语,典流于昆嗣,言列于汉籍,诚雄心所绝极,至精之所想遘也夫。” 这个义项传承至唐宋,元明以后日渐式微,迨及近代而遭遗忘。
大略在古汉语“汉籍”逐渐消亡之际,日本词汇“汉籍”传入中国。推想开始仅在涉日人员等小范围流通,真正进入大众视野则是比较晚近的事了。比如,清人姚文栋在《答近出东洋古书问》中提到日本富藏中国古书,“而明治维新以后,西学兴而汉籍替,世禄废而学士贫,将不能保其所有,其流落归于撕灭者,翘足可待也!”再如,清末大儒章太炎在《文学略论》中责难日本学人读书偏颇:“日本人所读汉籍,仅《中庸》以后之书耳,魏晋盛唐之遗文,已多废阁。至于周秦两汉,则称道者绝少,虽或略观大意,训诂文义,一切未知,由其不通小学耳。”考两人行实,姚文栋1881年曾出使日本,章太炎自1899年多次东渡,他们以“汉籍”指称中国典籍,显然带着些日本学界的色彩。
在日本语境中,“汉籍”大致有以下几个义项:(1)相对“国书”(日本人撰写的书籍)而言,指中国人撰写的汉文典籍,这是狭义的;(2)相对“和书”(用假名撰写的书籍)而言,包括日本的汉文典籍,这是广义的;(3)相对“佛书”而言,指佛学以外的汉文书籍,尤其指儒学典籍。举例说,日本人读“汉籍”,多用长安一带的“汉音”,诵“佛经”则多用江南一带的“吴音”,两者泾渭分明,绝不混淆。
然而,这个词汇一旦在中国落地生根,马上显示出巨大的生命力,与日本“汉籍”的原义渐行渐远。姚文栋所言“汉籍”,相对于“西学”著作;章太炎所言“汉籍”,接着“彼论欧洲之文,则自可尔,而复持此以论汉文。吾汉人之不知文者,又取其言以相矜式,则未知汉文之所以为汉文也”文脉,也与西学有关,已非日语“汉籍”之原义。时至今日,中日两国学者聚集一堂谈论“汉籍”,往往南辕北辙,甚至产生摩擦。
概言之,中国目前使用的“汉籍”,既传承古汉语基因,又吸纳日语词血液,经扬弃而创制出一个新词——不仅包括中国传统的经史子集,还涵盖佛经及章疏、变文之类,甚至有人建议将简帛、碑刻、尺牍、图赞之属,凡传递汉字文化信息之载体尽纳其中,以构架面向未来的新汉字文化圈。
国际视野
如上所述,在中国语境中,古代称书籍为“书”或“典”或“籍”,而冠以“汉”字而言“汉籍”,祖冲之是为区分上古之“唐典”,扬雄或有意峻别于新莽之“新籍”(参照前引张震泽《扬雄集校注》);在日韩语境中,日本学人言“汉籍”是在自家的“和书”出现之后,朝鲜半岛称“汉籍”乃为对应本国之“韩籍”。由此可见,“汉籍”概念萌生的契机,前者是在时间上被相对化,后者则是在空间上被相对化。
中国传统的汉籍研究,习惯在时间序列中上下求索,而当吾人视线指向空间,蓦然发现其外延早已扩伸至域外,“汉籍虽发源于中国,但已非中国所独有”。这门千年传承、百炼成型的“国学”,正演变为学科交叉且跨越国界的“东亚学”甚至“国际学”。从“汉籍”到“域外汉籍”,正昭示这一趋势。
然而,任何一门新兴学科的诞生,均必须构架严谨的学理基础;尤其是一门国际性学科,获取相关国家学人的共识,亦属必不可缺之前提。这里仅就“域外人士撰写的汉文著作”之范畴略加探讨。
张伯伟主张所谓“域外人士”,包括“朝鲜半岛、日本、琉球、越南、马来半岛等地的知识人,以及十七世纪以来欧美的传教士”。韩国留学生朴贞淑撰文与乃师商榷,指出东亚知识人的汉籍与西方传教士的汉籍不能相提并论,理由是“第一,从文化主体的立场来看,前者是参与汉文化圈的周边国家的文化产物,而后者却不是。第二,从文字的性质来看,前者是汉文化圈的共同语言,而后者只不过是当时的白话而已。第三,两者所撰写的主要目的也明显不同”。
此番言说颇值得倾听,但也有些偏颇之处。诚然,东亚的域外汉籍,不唯创作者是域外人士,原创地和传承地也在域外;而西人的汉文著述,大多有华人参与创作,原创地和传承地均在中国,与其说是域外汉籍,更接近中国汉籍。有关此点可作参照的是,往古众多天竺人参与译经事业,大量汉译佛经习惯上归入中国典籍。至于说西人的著述俱为“白话”,则有以偏概全之嫌。
我们再回到东亚。张伯伟提到日本学者往往将本国人用汉语撰写的典籍称作“准汉籍”,此“准”字似乎暗示低一档次。朴贞淑指出“准汉籍”并非贬称,原因是文化圈的中心国只有一种语言,而周缘国家则使用双语(中心语与本国语),因而“日本所称的‘准汉籍’,只不过是为了和中国‘汉籍’相区别而已。韩国也有‘汉籍’和‘韩籍’,这是汉文化圈周边国家之共同的文化现象”。
上述两位所称“准汉籍”系日本汉籍的说法,在日本学术界并非主流。虽然有些熟悉中国文献学的学者,把日本汉籍称作“准汉籍”,以对应正统的中国汉籍;但也有些日本学者着眼于本土文化,将本国人士撰著的汉文书籍,从文体上区分为“纯汉籍”与“准汉籍”,前者一依汉文规范,后者夹杂日语文法。在日本享誉汉学研究重镇的二松学舍大学,2004年获准创建全国唯一的“日本汉文学研究”国家基地,其标志性成果是构建了“日本汉文文献目录”数据库,按“日本汉文”、“和刻本汉籍”、“准汉籍”分类,对“准汉籍”定义如下:“汉籍本文经日本人加工,从而改变了原本的形态……比之和刻本汉籍,日本人加工的痕迹尤为明显,所以更接近日本汉文。” 这大概是目前日本学术界最专业的定义,可作为借鉴。据此,“汉籍”(中国汉籍)与“日本汉文”(日本汉籍)是对应概念,“和刻本汉籍”类乎“汉籍”,“准汉籍”则接近“日本汉文”。
域外人士累代创造的数以万计的汉籍遗产,无疑是域外人士的精神发露,根植于异域土壤,汲取异域的历史养分,因而研究的起点在域外;与此相对,中国汉籍在域外的延伸扩展,尔后被抄写刊刻乃至注释考据,属于发自中国源头的分流,所以研究的基点在中国。两者互相辉映,蔚成景观。
总之,“汉籍”从中国传播到东亚,又从域外回馈至中华,再经两岸学者呵护,升华扩容为超越时空的“域外汉籍”新概念。如此环流吐纳而生生不息,中国文化的精髓在斯,东亚文化的真谛亦当在此。笔者在此建议,“汉籍”为不分时代、不别国籍、不拘种类、不囿内外之总称,中国人原创称“中国汉籍”,日本人原创曰“日本汉籍”,以此类推。由此,既可彰显中国文化普惠四邻之辉煌,亦可观摩东亚各国孜孜不倦之创意,庶几臻于“和而不同”之理想境界。
来源:王勇:从“汉籍”到“域外汉籍”